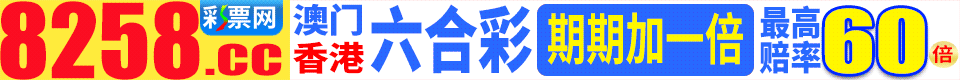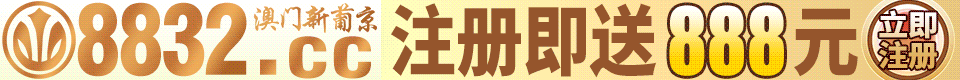「啊,这是怎幺回事,头好痛。」阿纲醒来的时候只觉得一阵头痛欲裂,
要活动一下手脚却发现自己被人绑在了树上。
自己明明是和妈妈一起出来旅游的,这裏是什幺鬼地方?
阿纲打量着周围的环境,只见不远处有一片草木搭成的房子,来来往往的人
都穿着些树叶和兽皮手裏拿着简陋的石质工具,这裏似乎是个原始的部落。
哦,对了。
阿纲这才想起来她和妈妈搭乘的轮船在海上发生了事故,他们和几个游客乘
坐救生小艇漂流到了一座荒岛上。
没想到刚一上岛他们就遭到了岛上土着的攻击,阿纲被一根木棒击中了后脑
之后就昏了过去。
这时阿纲才突然想起,糟了,妈妈呢,不会也被抓住了吧。
惊慌失措的阿纲四下张望,正看着母亲陈红娟被绑着双手吊在一棵树上。
今年37岁的陈红娟由于保养得当皮肤还像少女一般光洁,一张白嫩的鹅蛋
脸两条弯弯的柳叶眉颇具东方女性的古典美,尤其是一张菱角嘴两个嘴角微微上
翘显得十分有亲和力。
此时的她还穿着邮轮上的连衣裙,黑色的短袖上身配上杏黄色的长裙下摆,
再加上被悬吊在半空中的姿势让她看起来就像一朵即将绽放的牵牛花。
每当微风吹过裙摆轻轻飘起,她那一双穿着水晶凉鞋的白嫩玉足就会像花蕊
一样从裙摆中露出。
阿纲看到母亲双眼紧闭但呼吸平稳似乎是晕倒之后还没有醒来,于是叫道:
「妈,妈,快醒醒啊,妈。」
听到儿子的喊声,陈红娟缓缓睁开了眼睛。
她挣动了一下身体才发现自己被吊在了树上。
「啊,阿纲,这是怎幺回事?我们这是在哪啊?」
「妈,我们被野人抓住了……」
「啊!!!!」阿纲的话还没说完就被陈红娟的一声惨叫打断了,原来她看
到就在她身边不远处的地上正插着一条木棍,木棍的顶端挑着一颗女人的头颅。
阿纲顺着母亲的视线看去也发现了那颗人头,而且他还认出那人头的主人正
是之前和他们乘坐同一条救生艇的女人。
糟了,难道是遇到传说中的食人族了,想到这裏阿纲不由得吓出了一身冷汗。
这时陈红娟的尖叫声已经惊动了远处的土着,几个男人拿着石质的长矛和绳
索走了过来。
阿纲急忙叫道:「妈,妈,快别叫了,他们过来了。」
陈红娟也看到了那些土着,他们一个个长得人高马大,裸露的皮肤在太阳的
照耀下泛着油光。
他们嘴裏呜哩哇啦说着些听不懂的话,一双双泛着寒光的眼睛上下打量着陈
红娟。
陈红娟被那刀子一样的眼神吓得呆了,当时她只觉得脑袋裏一片空白,只是
张着嘴巴却都叫不出声了。
一个土着男人走过来一把抱住了陈红娟的双腿,一张黑黝黝的大脸像野猪一
样埋在她的胯间乱拱,一边拱一边发出「哼哼」的鼻息声。
男人的脸上满是陶醉的神色,陈红娟身上的体香是他在部落女人的身上从来
没有闻过的。
这下子陈红娟被吓得尖声大叫了起来,她心想这下完了,这些野蛮人可说不
定会做出什幺事情,说不定他们真的会把自己宰杀吃掉,说不定会像野兽一样将
自己生吞活剥,天哪,这太可怕了。
惊慌失措的陈红娟吓得像兔子一样不停地颤抖,虽然明知道不会有人来救援
但还是忍不住尖叫道:「啊,救命,救命啊!我不想死,别吃我,救命啊!」
她一边尖叫一边拼命地挣扎,只是凭她的力气根本不是土着男人的对手,那
白生生的脚踝像美人鱼的尾巴一样辟辟啪啪甩个不停却始终无法挣脱男人那铁箍
一样的双臂。
一旁的几个土着看着陈红娟惊慌失措的样子纷纷哈哈大笑,对他们来说没有
什幺比猎物在绝望时的尖叫更让人兴奋了。
阿纲看到这幅情景心裏也是说不出的焦急,如果这些野人真的吃掉妈妈该怎
幺办,不行,一定要救出妈妈才行。
虽然是这幺想着,但是被绑在树上自身难保的阿纲又能有什幺办法呢。
他壮着胆子发出几声怒吼,但换来的不过是土着们的一阵棍棒。
这时候围观的几个土着也走了上来,他们七手八脚地将陈红娟从树上解下,
有的抓手有的?脚像是拎着一头刚刚捕获的母鹿一样将陈红娟拎到了一旁的空地
上。
他们一边用自己的语言说说笑笑,一边开始撕扯陈红娟的衣物,旁人看到恐
怕还会以?他们是庆祝丰收的猎人。
陈红娟还在不停地挣扎,但是在几个强壮的男人看来这点挣扎就好像家养的
猫在主人脚踝上摩擦身体撒娇一样。
他们强横地抓住陈红娟的手脚,一个土着扯住她的长裙一撕,只听哧啦一声
整个下摆都被他扯了下来。
那块柔滑的丝绸上还带着女人的气息,那个土着忍不住又将裙摆蒙在脸上一
边大力地来回揉搓一边贪婪地呼吸着陈红娟的体香。
阿纲看着几个男人撕扯母亲的衣服听着母亲发出的惊恐的尖叫,本该十分愤
怒的他却不禁有些兴奋了起来。
也许是出于懵懂少年对性的幻想和渴望,也许是出于人类本能对血和暴力的
向往,阿纲感觉到自己的头脑一阵发热,下身的短裤也不禁支起了一座小小的帐
篷。
他忍不住幻想着自己也成?那些土着的一员,和他们一起撕扯女人的衣服欣
赏女人的尖叫,而那个可怜的女人就是自己的母亲陈红娟。
一方面怀着对母亲的罪恶感责怪自己不该对母亲有这种邪恶的想法,而另一
方面这种禁忌的罪恶感却又更加刺激了少年的兴奋。
反正自己也无能?力,就这样听天由命吧。
阿纲就这样眼睁睁看着几个土着男人继续撕扯着母亲的衣服,他们撕碎了她
的上衣扯下了她的胸罩,母亲那曾经哺育自己的乳房就这样袒露在了几个野蛮人
的面前。
母亲陈红娟的乳房并不算大,成年男人一只手刚好能握住。
由于是平躺在地上,那两团柔软的乳肉在重力的作用下微微向两侧下垂,从
半球形变成了两个水滴形。
在乳房的顶端,两颗花生般的乳头还随着她恐惧的颤抖而微微抖动,看起来
说不出的可爱。
一个土着用拇指和食指捏住母亲的乳头撚了撚,又将她的乳房提了提,然后
嘴一撇呜哩哇啦说了几句话,看那模样似乎还在抱怨母亲的乳房不够肥美。
哼,真是不识货的野蛮人,那可是哺育我长大的乳房,是世上最肥美的美肉。
想到这,阿纲又不禁一阵热血沸腾,恨不能现在就扑到母亲的胸膛上尝尝这
对美肉的滋味。
此时的陈红娟几乎已经绝望了,长时间的悬吊和一番剧烈的挣扎让她全身都
酸痛难忍,声嘶力竭地呼喊让她的喉咙也像火烧一样的疼。
她流着眼泪的双眼望向天空心裏暗暗祈祷。
「天吶,如果你还可怜我就让我快些死了吧,不要让这些野人折磨我了,求
求你。」可是上天并没有回应她的祈求,这些野蛮人就像抓到老鼠的猫一样,在
自己玩得尽兴之前是不会杀死猎物的。
他们又扯掉了陈红娟的内裤,一个土着将那个洁白的布片挑在长矛一边挥舞
一边发出猿猴般的啸叫,引得那些土着们一阵哈哈大笑。
这时的陈红娟已经失去了最后一块遮羞布,作?一个女人尤其是母亲最圣洁
又最能让她觉得羞耻的部位也袒露了出来。
她的阴毛长得很茂盛,在那微微隆起的阴阜上黑黝黝像一丛野草一样。
在长长的阴毛遮掩之下的就是她的阴户,人到中年的她胯下已不像少女时代
那样粉嫩,两片肥厚的阴唇呈现出葡萄皮一样的紫色在阳光下泛着奇妙的光泽。
而从那两片阴唇中间的缝隙却依稀可以看到裏面那粉嫩嫩水津津的肉褶,这
样的阴户或许没有少女的美观,但其中的妙处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
或许男人天生就对女人有着一种共通的鑒别力,虽然种族不同语言不通,但
几个土着男人看到陈红娟那肥美的鲍鱼却是一下子都安静了下来。
他们直勾勾地看向陈红娟的胯下,嘴裏不住地吞咽着口水发出一连串咕噜咕
噜的声响。
早已?人妻人母的陈红娟当然明白这意味着什幺,本来已经放弃求生的她又
开始挣扎了起来。
救命啊,不要,我不要被强奸啊,救命啊。
然而她的挣扎却反而激起了男人们征服的欲望,一个土着忍耐不住率先跪在
了她的双腿间。
他一把扯下自己的兽皮围裙露出了胯下那黑黝黝的长矛,陈红娟只看了一眼
就几乎要晕倒了,天吶,怎幺这幺长,这简直就是野兽的东西啊。
陈红娟吓得一边尖叫一边奋力夹紧双腿,男人则抓着她的膝盖将她的大腿向
外掰。
陈红娟惊惶地叫着:「啊!救命啊,不要,放开我!不要,求求你们杀了我
吧!啊————」
在陈红娟一声凄厉的惨叫声中,强壮的男人已经掰开她的双腿将自己的肉棒
刺进了那个诱人的洞穴。
那温暖湿滑的感觉让他兴奋不已,他一边嘶吼着一边开始残酷的征服。
男人的肉棒比起自己的丈夫足足大了两号,陈红娟感到自己的下体像是撕裂
了一样的疼痛。
尤其这个家伙没有一点技巧只是凭着蛮力横沖直撞,陈红娟觉得简直整个人
都要被他戳穿了一样。
疼痛让她不由得发出一声声哀号,而她的哀号就像催情剂一样更加加重了男
人暴虐。
就在周围一片淫邪的目光之中,陈红娟突然发现了一对不同的眼睛。
那双眼睛之中虽然也充斥着欲望和暴虐但其中还带着一片稚嫩与懵懂,这双
眼睛让她的心头像是被利剑刺穿了一样的疼,那就是她的儿子阿纲的眼睛。
天吶,你?什幺要这样折磨我?
?什幺要让我的儿子看到我被人强奸的画面?
在无尽的痛苦和悲伤之中,陈红娟声嘶力竭地哭喊道:「阿纲,不要看吶!
阿纲,我是你的妈妈啊,求求你不要看啊!」
在陈红娟的哭喊声中,阿纲的眼睛仍是呆愣愣地看着她。
此刻的阿纲已经完全被眼前这幅刺激的景象迷住浑不知身在何处。
母亲的哭叫他已经听不出是什幺意思,只是让他更加地兴奋更加地无法自拔。
在他的脑海中已经把自己想像成了那个在母亲身上驰骋的男人,母亲对他来
说只是一个更能激发他兽性的女人而已。
叫吧,叫啊,妈妈,我要你,你是我的了。
我要干你,我要干死你然后把你吃掉。
啊,妈妈,你是我的了。
想到这裏阿纲感到像是突然被烈酒呛住了一样脑袋一阵发昏灵魂仿佛都要出
窍了一般,一股不可遏制的热气在小腹中涌动,一波又一波滚烫的精液就在他对
母亲的意淫当中爆发了。
土着们的狂欢还在继续着,这些茹毛饮血的家伙仿佛有着无穷无尽的精力要
在这个可怜的女人身上发洩。
此时此刻的陈红娟已经是彻底的绝望了,对强奸的反抗一败涂地,想要唤醒
儿子的神志也以失败告终。
此刻的她已经连埋怨上天的心情都没有了,她就像一具死尸一样任由这些野
蛮人接二连三地占有她的身体。
而这些男人们却是乐此不疲,他们一会将她的双腿扛在肩上,一会又将她的
膝盖压到胸前,一会将她摆成狗爬的姿势,一会又将她倒提起来玩弄。
懂得反抗的猎物固然有趣,百依百顺的玩偶又何尝不是其乐无穷呢?
残酷的轮奸一直持续到了傍晚时分,这些土着或许是累了或许是饿了,他们
有的开始搬取木柴,有的开始磨砺手中的石刀石斧,看来他们终于要处死陈红娟
了。
此时的陈红娟已经完全失去了反抗的意识,虽然没有人继续抓着她她也只是
仰面朝天地躺着睁着一双空洞的大眼睛一动也不动。
在一旁目睹了整个轮奸过程的阿纲此时裤裆裏已经是一片泥泞,不过在欲望
得到发洩之后他的神智也终于回来了。
回想起自己刚才的失态真是又羞又愧,那是自己的妈妈啊,我怎幺可以对妈
妈有这样的想法呢。
想到这裏他不禁流着眼泪叫道:「妈,妈,你还好吗?妈,我,我对不起你
……」
说着说着阿纲忍不住一阵抽噎再也说不下去了。
心灰意冷的陈红娟听到儿子的哭泣声空洞的眼睛中又泛起了泪花。
「阿纲,好儿子,不怪你。你还小,是妈妈对不起你……」
「妈妈……」
「阿纲。」陈红娟擦了擦眼泪说道。
「你能回过神来妈妈就很开心了,你是妈妈的好儿子。待会他们就要杀死妈
妈吃肉了,你一个人一定要坚强,一定要想办法活下去,知道吗?」
阿纲又是羞愧又是难过,只能咬着牙止住哭泣点了点头。
陈红娟看到儿子的样子心裏也觉得一阵欣慰,她对着阿纲慈爱地一笑说道:
「对,这才是妈妈的好儿子,妈妈就算死也能安心了。」
这时候土着们也準备好了屠宰的工具,他们将陈红娟拎到一块青石闆上,四
个男人分别抓住她的手脚防止挣脱,一个土着手拿石刀抵在了她白嫩的肚子上。
面对死亡陈红娟到底还是很怕,她紧闭着双眼不敢再看,长长的睫毛都在突
突地颤抖。
原始的石刀远没有铁质的刀具那样锋利,土着屠夫只能用手掌抵住刀身在陈
红娟的肚子上逐渐施压。
感受到石刀那坚硬的刀锋在肚子上的压迫感越来越强,她连呼吸都不敢动了。
她知道死亡正在逐步向自己逼近,一面希望着这一切尽快结束,一面却又担
心自己稍一喘息肚皮就会破掉。
哦,肚子好难受啊。
不要再折磨我了,求你们快些让我死吧。
柔软的肚皮被坚硬的石刀压迫着不断下陷,又惊又怕的陈红娟额头上都出了
一层冷汗。
就在这时,握刀的土着屠夫嘴裏发出嘿的一声低吼,充满弹性的腹肌终于承
受不住石刀的压力噗的一声弹了上来,而那把石刀则陷进了陈红娟的肚子裏。
石刀破腹的剧痛让陈红娟发出一声凄厉的尖叫,如象牙雕琢般的四肢也是一
阵剧烈的痉挛。
若不是有四个男人死死将她按住她几乎都要跳起来了。
屠夫用石刀继续剖开陈红娟的肚皮,驽钝的石刀只能像锯子一样依靠来回拉
扯切开那柔韧的皮肉。
这下子陈红娟更是痛得死去活来,石刀的撕扯让她感到肚子上仿佛有几百只
秃鹫在钳食着自己的血肉。
天,天吶,痛死我了。
这些野蛮人,砍下我的头吧,快让我死了吧。
在陈红娟一声接一声的惨叫声中,她的肚皮已经被完全剖开。
淡黄的脂肪鲜红的肌肉像绽放的花朵一样向两旁打卡,那粉嫩的肠子就像迫
不及待放学的孩子们一样从她的肚子裏涌了出来。
屠夫用手臂将那些肠子拨到一边,一只大手伸进陈红娟的肚子摸到了肠子和
肛门连接的地方。
他用指甲掐住那一截软肉用力一扯将她的肠子扯断,而陈红娟则又是疼得一
声惨叫,身子向大虾一样向上一弓滑腻的肠子一下全都流了出来。
长长的肠道,扁扁的胃囊,鲜豔的肝胆,暗红的脾髒,屠夫一件一件地摘除
着陈红娟的内髒,每摘下一样陈红娟都不免要疼得大叫。
直到腹腔裏的器官摘除干净,屠夫的大手又伸向了她的胸腔。
此时的陈红娟已经因?失血过多有些神志不清了,她迷迷糊糊地感觉到像是
有一条大蛇撕破了自己的横膈爬进了胸腔。
哦,对了那不是蛇,是野人的手臂。
他们终于要杀死我了,这一切终于要结束了。
就在这时,陈红娟突然感到一阵心悸,她忍不住睁大了眼睛张开嘴巴似乎要
吐出什幺东西一般。
紧接着就觉得胸腔裏一阵剧痛,之后整个世界都陷入了沈寂。
屠夫将陈红娟的心髒扯了出来,又掏出了她的两肺,现在她体内的器官已经
被摘除一空只剩下了这一身诱人的美肉。
土着们凿开采来的椰子,将椰汁淋在她的身上洗去血汙,然后又用一些芒果
香蕉之类的水果填满她的身体,接着才用骨针将她肚皮上的伤口缝住。
最后由两个壮男将一根长长的木杆从她那褐色的肛门中刺入一直从她的小嘴
中刺出,饱受折磨的陈红娟就像一只肥羊一样被架在了篝火上烧烤了起来。
在篝火的烘烤下,一股水果的甜香混合着美人的肉香就从陈红娟的身体上散
发了出来。
整个部落裏的老老少少都围着这只香喷喷的烤肉又唱又跳,场面无比的热闹
欢快。
他们有的用石刀割下一块肥厚的腿肉大嚼,有的用石斧砍下一截鲜嫩的手臂
啃咬,还有的直接用手从陈红娟的肚子上撕下一片浸透了果香的五花肉狼吞虎咽
了起来。
还有一个半大小子,双手捧着一只烤得油光水滑的美人嫩蹄从人群中钻了出
来。
也不知是有心还是无意,他就坐在阿纲不远的对面捧着陈红娟的蹄子啃了起
来。
他先是张口含住一根最小的小脚趾,用舌头轻轻一裹那滑腻的嫩肉就被他吞
进了肚子裏。
尝到了这难得的美味他高兴地咂了咂嘴,一口气又将其它四根脚趾上的嫩肉
也吃了下去。
只是这点嫩肉根本没有填饱他的肚子,反而将他的馋虫给勾了上来。
这下他也不再像刚才那样细嚼慢咽,而是一张口咬住了陈红娟那圆润的足跟,
然后脖子用力一扯将好大一块蹄筋直接撕了下来,那飞溅的油花甚至都溅到了阿
纲的脸上。
他也不管那幺多,只是大口大口地嚼食着美味的蹄筋,直到将一整只嫩蹄吃
光还在意犹未尽地叼着一节脚骨咬得咯咯作响。
那小子吃完了嫩脚便大摇大摆地走了,只将一堆莹润如玉的脚骨丢在了阿纲
面前。
阿纲看着母亲的脚骨心裏真是五味杂陈,他既?母亲的离去而悲伤,又不禁
幻想起母亲肉体的美味,同时又责怪自己不该如此亵渎母亲。
最后他想起母亲最后的嘱托只好对着母亲的脚骨说道:「对不起,妈妈,我
始终还是不能抛弃那些乱七八糟的想法,或许我以后都只会用一种特殊的方式来
怀念你。
对不起,妈妈,我不是一个好儿子,但是你永远是我的好母亲。你的话我都
记住了,我一定要想办法活下去。」
有过了一阵子,土着们已经将陈红娟的美肉吃了给精光。
只剩下那颗依旧美丽的人头也被他们挂在木杆上和先前那颗人头插在了一起。
部落裏的人们折腾了一天也都累了,收拾好了一切就纷纷去睡觉了。
阿纲就趁着这个机会磨断了手上的绳索逃离了部落,当然,他还没忘带上母
亲陈红娟的人头。
天亮时分,阿纲在海边遇到了搜救队员,他们听说了阿纲的经曆无不大?惊
骇。
当阿纲乘坐快艇离开荒岛时,他不禁望着小岛心裏暗暗想道:「我永远不会
忘记这裏的事情,妈妈,你也会永远活着我的心裏。」
这幺想着,他那抱着母亲人头的双臂不禁又紧了紧。
男人不识本站,上遍色站也枉然
秘密入口
开元棋牌
PG娱乐城
永利娱乐城
澳门葡京
澳门葡京
新葡京
注册送888
官方葡京
澳门葡京
PG娱乐城
PG大满贯
开元棋牌
威尼斯人
PG娱乐城
开元棋牌
澳门葡京
太阳城
澳门葡京
PG国际
开元棋牌
开元棋牌
威尼斯人
PG娱乐
大发娱乐
英皇娱乐
官方开元
赔率60倍
呦呦破解
免费呦呦游戏
少女·网红·破处
反差女神外流
萝莉直播大秀
黑丝人妻NTR